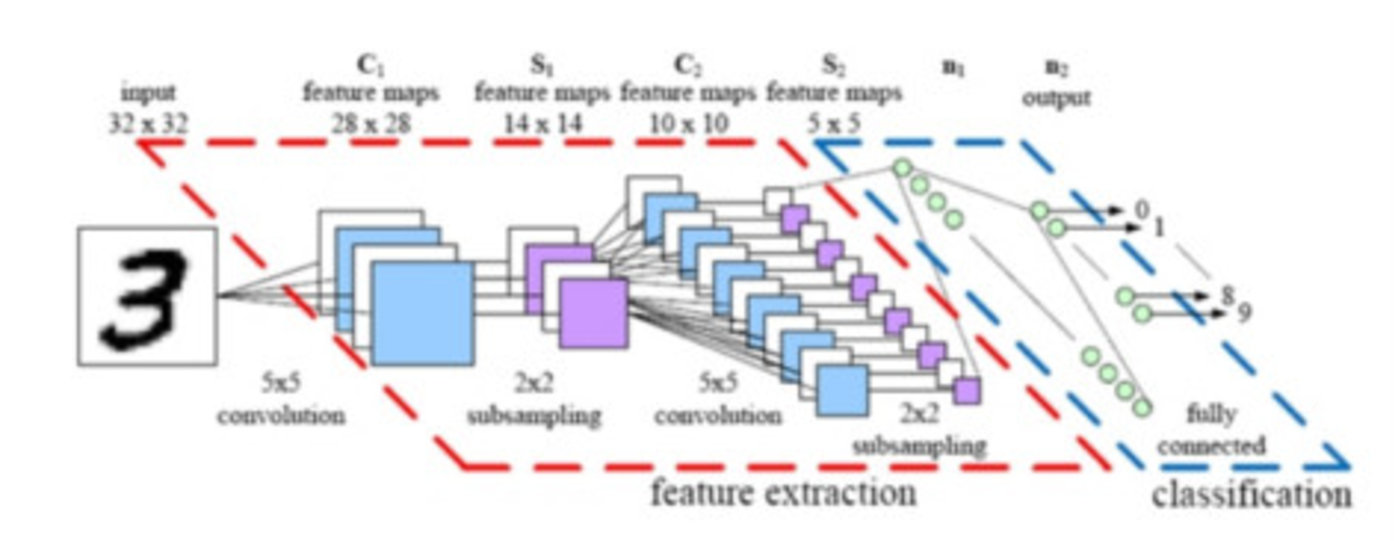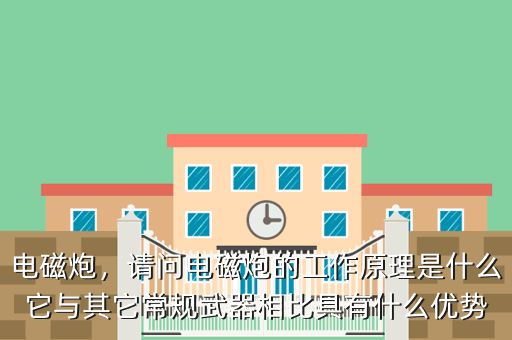请让我听你——百年听诊
医学生都知道听诊器的“魅力”。
刚进入医学院校时,望着高年级同学衣袋里放着听诊器,心里特别羡慕。有同学可能会说,买个不就满足了吗?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追求的是“正规”地满足,需要的是那份认证。
进入大学三年级,接触到了诊断学这门学科,终于有机会使用听诊器了。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甚至幻想在学校的公共浴室里也能挂着一个听诊器。
后来学起内科,才明白这听诊器其实挺没意思的。那时拿着“便携式播放器”一个劲儿练“听觉”,老反复听“异常心跳”的录音带。可听诊测验结果还是一窍不通:里面全是些啥啊…
要真正熟练地“运用”听诊器,并非短时间内就能掌握,确实非常困难。1929年,民国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就下达“命令”:没有合法行医身份的人,禁止使用听诊器。这表明:不到精通程度,也不配使用听诊器!
不过,听诊器的内涵,绝非仅限于技术。
1911年,在上海出版的《医学新报》上,有一篇题为《听诊器之得失》的文章,其中对当时五种听诊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最终指出,带橡皮管连接的听诊器最为出色,不仅听诊效果显著,而且使用时能更好地维护患者尊严,尤其适合为身份尊贵者及女性进行诊断。
咱们就从失礼这事开始聊聊听诊器。
Laēnnec的听诊器
估计很多人在小学里就听说过这个“发明听诊器”的故事。
在听诊器发明之前,医生们运用的是“直接听法”。他们把耳朵紧贴在患者躯体上开元棋官方正版下载,以此方式来听诊。
十八一六年,法国医学家Laēnnec在诊疗一位贵族女性时,觉得直接听诊的方式不太方便,于是寻思着替代方案,他取来一张硬质纸张,将其弯折成一个圆筒状,一端放置于患者胸膛部位,另一端则贴近自身耳畔,借此成功实施了听诊。有人或许会质疑,法国人难道也如此保守吗,这确实值得深思。中国人观念更为保守,过去我们上诊断学这门课的时候,同学们分组练习听诊,连男女搭配都不被允许,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直接听诊法,确实有点儿不雅)
(羞涩的Laēnnec和他的女病人)
后来,Laēnnec尝试了多种物料,历时数年试验,最终成功打造了全球首个木质听诊工具。1819年,他推出了一部篇幅颇大的著作:《关于借助迂回探测方式及主要采用这一新方法诊断心脏与肺部病症的论述》,“迂回探测方式”因此广为人知。书中详尽阐述了听诊工具的构造机理,并且该书与听诊器捆绑销售。有经营意识呢,好比发行一部《放射学诊疗基础》来配合销售CT设备,此人做医生实在是屈才了…
再后来,人们不断地对听诊器进行升级改造。
1828年,听诊器的钟件变成漏斗形,耳件变小。
1843年,双耳听诊器出现。
1851年,听诊器胸件上安装了有弹性的薄膜。
1855年,双耳听诊器出现了可弯曲的管子。
1894年,一种配备固体振动装置的听诊仪面市,被称作“放大声音听诊仪”。(提及“放大声音”,我内心不禁产生感慨。记得当实习医生期间,同住宿舍的妇科和心内科同事在楼下下棋,这时心内科的伙伴拿着新买的听诊仪过来,在门口炫耀说:“这个放大声音的功能很棒…”妇科的伙伴一边下棋,一边莫名其妙地接话:“放大阴部效果如何?明天借我用用,去诊疗室做检查。””医学生的快乐你不懂…)
1925年,出现了将钟件与硬质震动膜整合的胸件,听诊器至此完成定型。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直接听诊和间接听诊是同时存在的两种方法
这就是那位名家的《关于中介式听诊及其主要应用来诊断肺部和心脏疾病》这本书
(最初的听诊器kaiyun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就像笛子,所以也叫“医生之笛”)
(后来,就改进了)
早些时候,拥有一台听诊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位医生手头有两台听诊器,真够奢侈的...
(这件古董听诊器绝对是艺术品啊)
后来,听诊器慢慢固定了形态。世纪初曾有两个听头的听诊器,号称能分辨出“双耳音效”。真没想到,想法再大胆也有实现的可能。
听诊的未来
听诊器在不断的发展。
2012年,墨尔本大学有四位学生开发出一种创新式电子听诊设备,该设备内含录音装置,能够方便地把患者检查情况传到手机上,供医生进行远程诊疗,他们因此赢得了当年的微软创新杯。
目前,融合蓝牙等多样特性的电子听诊器已投入医疗实践,通过听诊能够采集到的数据持续增长。
这些年,我接触过部分探讨听诊问题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多数以患者视角切入,指出当前诊疗过程中,不少医师不再实施听诊,转而直接开具各类化验和检查申请单。部分人将此归咎于医院“重检轻医”的策略;也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当前医师的临床基本功有所欠缺。这些现象确实都客观存在。然而,它们或许并非症结所在。对于众多患者而言,进行听诊能够起到交流作用,同时也是医护人员给予的一种抚慰。如果没有听诊环节,他们就会觉得医疗过程不够完整。
众所周知,未来某天kaiyun.ccm,机器将能独立完成听诊任务并给出诊断结果,届时,听诊这种传统诊断手段的价值将被更先进的检测方法彻底取代。
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因此,眼下,不论从诊断层面,抑或从人道主义视角,我们都必须努力执行“听诊”这一医疗不可或缺环节。各位同事,请戴上你们的听诊器。
有人或许会疑惑,当听诊器彻底失去用途之后,我们如何向患者传递人性温暖呢?
我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也许,这个答案,需要经过漫长的时光洗礼,才会最终呈现给世人。它的诞生,就好比听诊器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完善的历程。
这个听诊器价格不菲呢。记得从前在儿童诊疗机构当见习医生时,那位负责诊疗的医生佩戴着个非常气派的听诊器。有位同僚透露,那件医疗器械是海外购置的,价值高达一千多元。我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地挨过去,恳求道:前辈,可以让我碰一下吗...
2012年,澳洲学子研制出一种可嵌入手机内的小型听诊设备,实现了数字化听诊功能。
“妈妈,我什么也听不见婴儿的动静了...啊,看来是我没戴上耳塞...”这些失误也是实习医生们时常犯的毛病。
授课时,每位教师都会强调,必须先让听诊器探头暖和,才能用它为患者检查,否则患者会像这个小猩猩那样。
1953年,有位法国眼科医生正在为婴儿进行体格检查,他运用了直接或间接的听诊手段,这背后都蕴含着温馨的关怀。
(让我们再一次向听诊器的发明者Laēnnec致敬)
(原文标题:请让我听你—百年听诊)